
《“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王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即将出版

《“零度”日本》的关键词是“少女”。无论是在隐喻还是现实指涉的意义上,这本书讨论的许多文化和社会现象,在主题层面上都与“少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然而,与此同时,本书所通向的决不是对于“少女”的理解,更不是对于“少女”的概念辨析或词义考古;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本自始至终都与“少女”无关的书。毋宁说,本书试图以“少女”这个称谓、范畴、符号甚至能指,打开或接近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奇特甚至诡异的空间,一个同时具有文学性、政治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空间,一个无法被既有学科体系——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化研究”或“亚文化研究”等所谓“跨学科”的学科体系——所充分对象化的空间。因此,“少女”在这里也可以被视为对于这样一种奇特空间的临时命名。在我看来,这种命名最终也可以帮助解释标题中所谓的“零度日本”。关于这一点,也许需要做一些说明。
让我们从一个切近的例子开始。当代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在一部关于几个高中女生的小说中,为其中一个女生设计了一篇独特的“作文”,其中有这么几段话:
《高中女生是什么样子》
要我们以高中女生是什么样子为主题写作文,老实说,我不知道到底出题人在探求什么。我也不是自己想成为高中女生而成为高中女生的,只不过是时候到了就升学罢了。我认为,自己是高中女生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年级的一个人说,这个命题作文“其实不是语文作业,而是受媒体或大学的委托所进行的高中女生意识调查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在成年男性里,有些人对高中女生的生态有着奇特的兴趣。
打开电视,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讨论高中女生之间的流行语和奇特的时尚之类。不过,最得到热议的,还是卖春等涉及“性”的不良行为。一说到这个话题,评论员大叔们的声音就会激昂慷慨起来。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对于高中女生在“性”问题上的不良行为侃侃而谈的大叔们,他们的表情显得过于亢奋,流露出莫明的喜悦,仿佛并不是真心为女高中生感到担心,而是——怎么说呢,像是在既享受又恼火地反复逗弄与自己疏远的小动物。
我觉得那帮人绝对不正常,因为他们一味地讨论女高中生的卖春问题,而不关心高中男生的卖春问题。将身体卖给女性或男性的高中男生就不需要担心了吗?(松浦理英子『最愛の子ども』,文芸春秋,2017年,第8-9页)
小说主人公之一今里真汐的这篇“命题作文”,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少女”成为社会关切之焦点的奇特方式。毋须多言,在近代日本的社会语境下,自从“少女”在明治以降作为一个被认定具有稳定指涉的范畴确立之后,随着现代教育制度和医学制度的确立,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政治主体的性别差异的规定,乃至对未成年女性在学校、社会和家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担任的社会分工的规定,有关“少女”的各种文化想象——从服装、外貌到行为规范——就不曾有过间断。关于“少女”近代以来如何在各种话语中得到表征,论者们可以(也确实已经)写出一系列研究。
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以现代原子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形象为出发点,有关女性的不同年龄段的文化想象和制度性安排——从着装、言行举止到自我身体的治理——都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对于“少女”的预期和认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概念的模糊边界和历史层累,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当代日本社会围绕“少女”所提出和前景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现象上,那么也很容易看到,当今书肆和媒体上由各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专家学者或记者所撰写的有关现役女高中生或女大学生因各种原因而参与软色情行业乃至非法卖淫的纪实类书籍,早已像快餐食品一般,俨然成为一种特定的消费品(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关于卖淫主妇、AV女优等“贫困女子”的纪实类书籍)。例如,当东京在2020年因为疫情而宣布紧急事态令之后,关于由此陷入贫困的卖春少女的书籍,一年内便出版了不下五种。在这些作者充满忧愁的笔调下,我们总是能看到他们对于采访对象所披露的生活细节的奇特兴趣,而他们从不同的受访者经历和不同的细节中,又总是能得出雷同的、大而化之的结论:政府政策的灰色地带、制度性保障的匮乏、社会关注的缺失、少女们的绝望。
这些现象本身或许无甚稀奇。重复一遍:自从“少女”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诞生的一系列文化符号和制度性安排在现代性条件下形成并稳定下来以后,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围绕“少女”话语的种种想象和讨论,总是容易成为论者们热议的焦点。与此同时,不要忘了,在战后日本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少女”作为一个文化象征,也曾不时被知识人拿来与他们对于革命的纯粹性或天皇的纯粹性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如批评家絓秀实指出的那样,“少女”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之所以能作为“革命的增补(的增补)”,是因为“这一存在既在‘性’的意义上,也在形象的意义上是纯洁的,与此同时又是进步而现代的。资本制带来的‘故乡丧失’必须经由纯洁的‘革命’得到恢复,贫困和饥饿却又必须由资本制的‘进步’来克服;‘少女’便将上述悖论集于一身”(絓秀実『JUNKの逆襲』,作品社,2003年,140-1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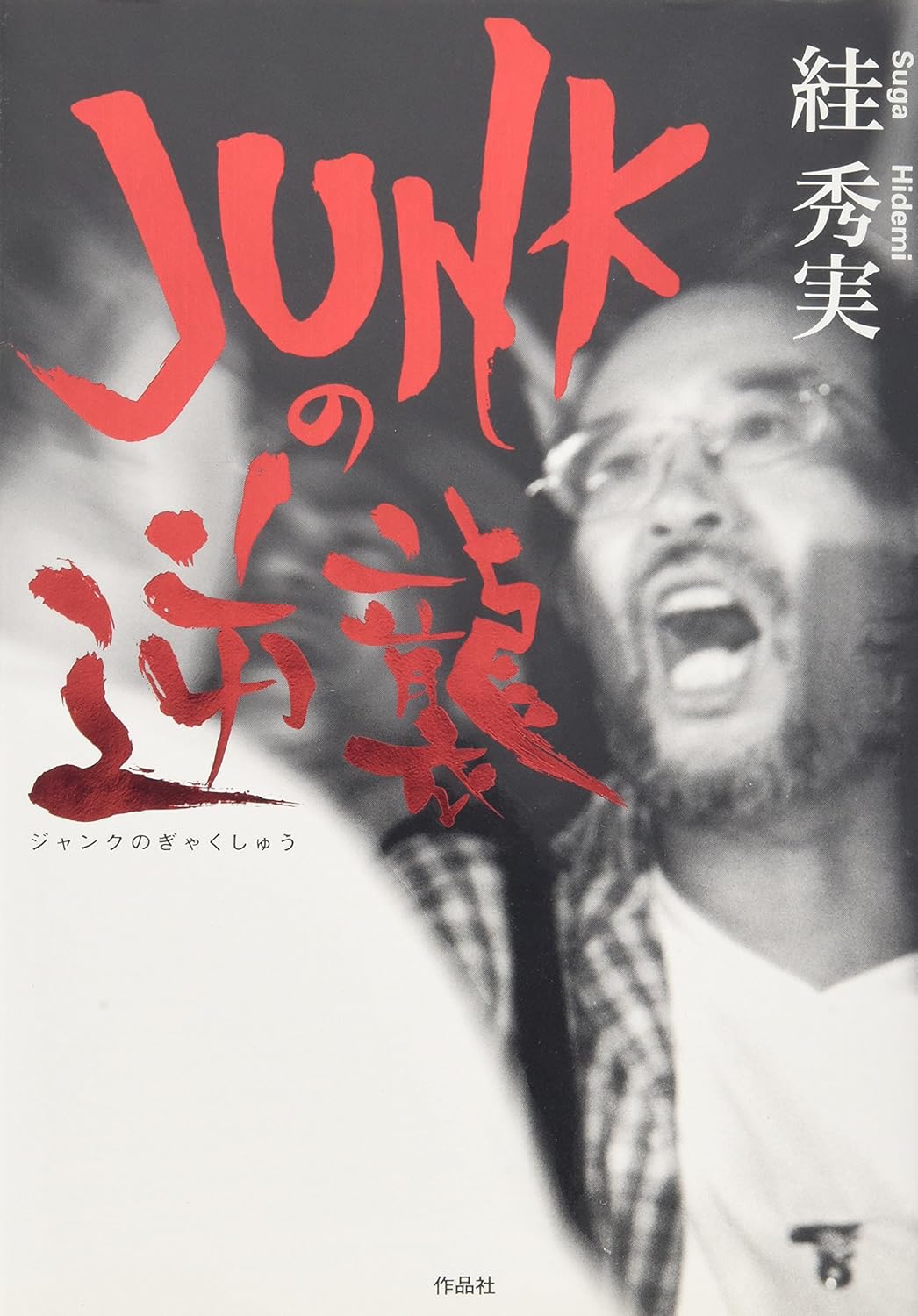
絓秀实著《垃圾的逆袭》
但是,正如絓秀实以思想家吉本隆明早期诗歌中的“少女”形象为例进行的分析所透露的那样,“少女”一方面作为一个被典型化的符号出现在文艺创作中,并由此进入理论和批评的视野,另一方面则往往在社会学的对象群体的意义上,被研究者们——尤其是被执迷于纪实采访的研究者们——还原为一系列社会问题或矛盾的被动受害者。无论是何种情况,人们似乎都没有办法就如下问题形成令人满意的一致答案:当人们在谈论“少女”的时候,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一边是“田野”(读作:搭讪[ナンパ])归来的“社会学家”绘声绘色地向读者描述着他们了解到的未成年少女的卖春行为,一边如吉本隆明等思想家们则激进地、想象性地为“少女”的符号赋予各种乌托邦色彩——这里呈现的与其说是“少女”的形象与指涉之间的分裂,不如说是侃侃而谈的“大叔”们的思想分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可以就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毋宁说,重要的是论者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分裂及其意义。)
距今二十多年前,以研究“援交少女”现象著称的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在一篇关于在日本东北青森地区从事“电话风俗”服务业的少女的研究报告的结尾,对于包括自身的研究在内的、针对以这些“风俗业”少女为主题的公共话语和学术话语,展开了一番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女性的人权”“人格的尊严”“孩子们的将来”等所谓“普遍性”语词,在这种地方都市的“本土”空间内,究竟如何传达、传达到哪里,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朝日文庫,2000年,49页)
如果说上述质疑仍然建立在“东京=大都市”/“青森=地方都市”的地域性二元格局之中的话,那么,宫台接下去的一段话则几乎以一种犬儒主义式的自我反讽,不仅从根本上取消了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在内的学术研究的意义,甚至取消了这篇研究报告本身的意义:
我在去年(1993年)《朝日新闻》文化版的“水手服论战”中批判说,“如今恰恰有必要确立现代市民的伦理”也好,“有必要确立主体性”也好,“有必要成熟起来”也好,“战后知识分子”挂在嘴上的这些语词,都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知识分子限定”、“论坛限定”的那种“讨好长辈”的戏言罢了,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安慰被现实——即背叛了知识分子们的表面说辞的现实——所伤害的自我意识。然而,这种结构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也已经渗入到我自己关于“水手服高中女生”或“约会俱乐部高中女生”的论述中去了,不是吗?(同前,51页)

宫台真司著《虚幻的郊外:生活在成熟社会的年轻人的去向》
无论是对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表征的研究者而言,还是对像宫台本人所做的那样,以社会学的方法和进路来分析一系列不太被学界关注的边缘性社会现象的研究者而言,上面这段批判都极为根本:宫台似乎在说,这些道貌岸然、整日忧心忡忡的学者,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乃至关怀被忽视的、脆弱的社会群体,但他们所使用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话语和概念,不仅无法传达到被分析对象那里,无法成为她们的慰藉和帮助,反而自律而自足地形成了一种限定在知识分子内部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的交流可以像资本一样顺畅运行并不断增殖。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不仅没有勾连起自己所关心的“少女”们(毋须多言,这里的“少女”可以替换为其他语词)和普遍性话语之间的分裂,反而在话语的层面上对“少女”们施加了另一重暴力。(事实上,也有学者更为“釜底抽薪”式地将包括宫台真司的论著在内的围绕[例如]“援交”现象形成的一系列知识话语,视为添油加醋地将仅限于一小部分高中女生的事例放大化乃至普遍化的始作俑者。例如,莎伦·金塞拉[Sharon Kinsella]试图通过援引各种数据来表明,宫台真司本人进行的田野调查其实充满了先入之见。参见Sharon Kinsella, Schoolgirls, Money, and Rebellion in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assim。颇为奇谲的是,宫台真司在论述中反复强调的“交流模式”,在金塞拉的批判性讨论中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我的最后这句论断也仅仅是“知识分子限定”“论坛限定”的一种“受虐式英雄主义”,因为实际情况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少女”也许根本就对这些知识话语漠不关心、置若罔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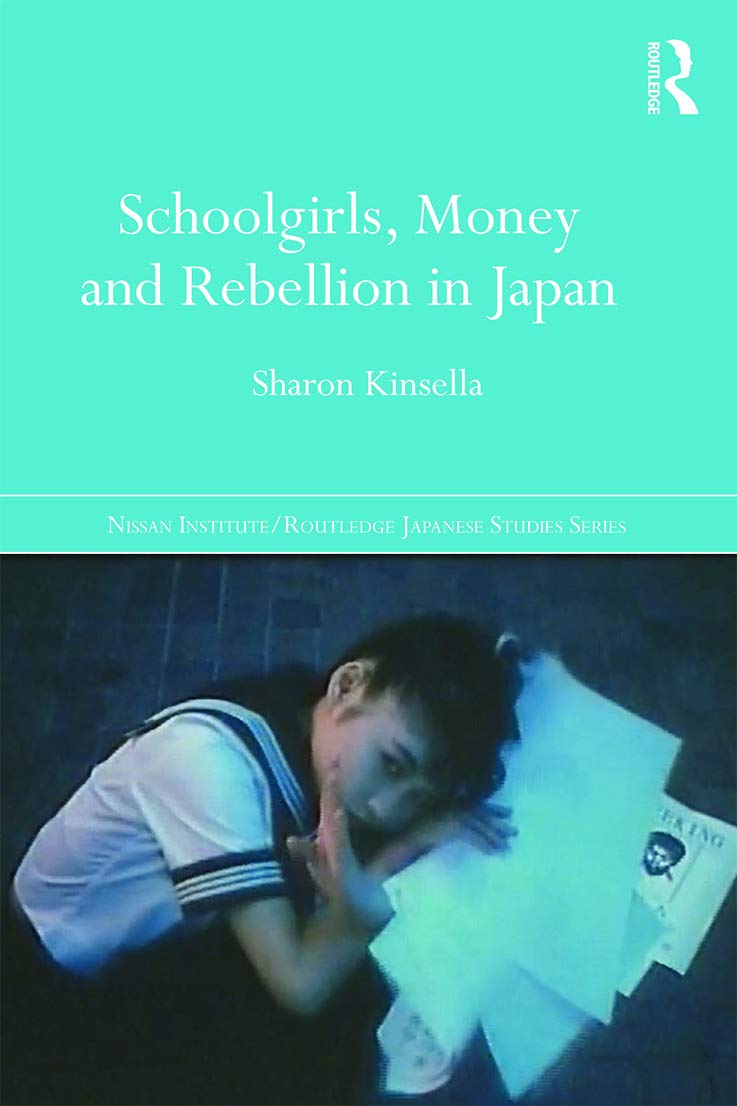
莎伦·金塞拉著《日本的女生、金钱与叛逆》
我愿意反复强调这一点:考虑到如今日本图书市场上充斥着以一年出版数本书籍的速度不断“消费”所关注和分析的对象——无论是从事AV摄制的单身母亲、援交少女还是“风俗女”——并千篇一律地使用“纪实”手法得出一些老套结论,继而对社会不公痛心疾首一番的“专家”或“学者”,不得不说,宫台真司的这两段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批判至今仍然有着迫切的现实相关性。大而化之地说,如何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自己的生活关切发生直接关联,或有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从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由于分析对象的差异性,着眼于“援交少女”等社会现象的学者,无疑比(例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古希腊哲学的学者更需要直面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宫台真司的(自我)批判,比起有意无意地拿这些所谓“边缘性”社会群体作为谈资和卖点的“学者”,至少来得真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自我)批判恰恰要求论者一方面克制甚至规避纪实性的写作,另一方面则要拒绝种种道貌岸然的“人文关怀”,拒绝站在某种可疑的道德高地上开出几味启蒙的“药方”。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宫台真司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否定研究分析的意义和价值,而是阐明了此类分析——无论是将它称为“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还是“文化批评”——所必然具有的性质:直截了当地说,这类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性。此话怎讲?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说此类分析是虚构的或没有现实对应物的,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中的“少女表征”来理解我们谈论或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显而易见,在今天,随着词源学考察和实证性的文本考据日益被当成学术研究的唯一前提乃至学术研究本身,看到“少女”一词而本能地想要回到如明治时期的文学和综合性报刊杂志上,寻找这个语词的“源头”,固然可以认为是一种受过“学术训练”的表现——无论在好的还是坏的意义上——但这种“专业操作”却丝毫无助于我们倾听和注意漫无目的地游走于深夜街头、以网咖为家的年轻人和她们特殊的交流模式,却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去倾听她们的学术理由。)毋宁说,“文学性”在这里的意思是,这类分析不能单单停留于它们所描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表意内容层面,也不能短路地从当代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话语中寻求对这些现象的直接解答,而必须着重分析这些对象或现象的语法结构、意义生成方式和背后所预设的种种社会和思想前提。因此,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一时一地的历史现场(事实上,为了抵抗研究者自身——无论性别——的某种“偷窥欲”,这种分析甚至必须在原则上拒绝上述纪实性的还原);毋宁说,这些文学性的分析必然要将视野从局部而特殊的语境扩大到“社会寓言”的维度,从而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认知测绘”(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为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交流模式提供自我反思的契机。——没错,努力尝试倾听和理解这些“少女”,最终是为了自我理解。甚至可以说,“少女”的不可理解性,恰恰将成为我们自我理解的可能性条件。这同时是这种分析的限度和可能性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分析必须也必然会把我们带向交流的“零度”、社会性的“零度”、政治的“零度”层面,迫使我们思考交流如何可能、社会关系如何可能、共同体如何可能,等等。
确实,这类分析所关注的社会群体,往往是一些在旁人看来脱逸了“正常生活”,却又不得不仍然继续生活的人们。当然,根本而言,就像之前引用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完全不必把焦点放在(与所谓“少年”相对的)“少女”身上——“少年”的不可理解性或许一点也不亚于“少女”的不可理解性(尽管我们不必因此继续引申,从而笼统把问题推到他者的“他异性”上面);不过,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媒体对于“少女”的执着聚焦和强调,往往使得她们作为社会问题的“症候”变得显豁,而社会加之于“少女”符号上的各类意指,又在漫长的历史中将少女们裹挟进各种复杂的文本网络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如快餐一般泛滥,并如快餐一般被读者消费的诸多纪实文学,就它们将少女们的生活搬上当今的历史前台而言,无疑有着相当程度的积极意义。很容易看到,这些少女对于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理解,乃至对于自己处境和选择的说明,往往在言语和逻辑层面上充满了矛盾、混乱和种种不连贯——分析者无法、也不该按照字面意思将她们的自我理解照单全收;对于她们的“阅读”,必须也只能是一种症候性的阅读。分析者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不是整理出这些自相矛盾、东拉西扯的自我论述背后的“一贯性”,也不是去提炼或总结她们的“思想”,更不是去“启蒙”这些有着复杂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少女。再说一遍:在分析中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分析者将她们的言行举止作为“症候”进行解释的时候,这些分析既无法成为对她们的直接帮助,也无法为她们带来任何慰藉。这些分析之于它们的对象,始终是外在的、陌生的、他异的,但决不是高高在上的。
在此,我们似乎绕回到了宫台真司的(自我)批判,并且不得不给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所有这些分析,对于徘徊在边缘的少女们而言,对于她们的复杂生活而言,对于她们随时都在逃避或挣扎的困境而言,都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且无法传达到她们那里。分析者对她们的关注乃至承认,除了呈现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有点惹人厌的凝视之外,什么也不是。但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这些分析——这些最终必须也只能指向我们的自我理解的分析——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指向的也许不是当下的拯救,而是未来的拯救或拯救的未来。
在这里,我们终于抵达了“少女”和“零度”这两个语词之间的关联:简言之,一切貌似具有普遍性、在言论的公共空间内畅行无阻的理论话语,都结结实实地遇到了几乎是物质意义上的抵抗——无论是以写实的方式用文字再现她们的生活处境,还是诉诸权利话语来主张她们的个体权益和社会福利,抑或是如上所述,以文学性的分析探究她们背后的社会和历史机制,对这些被关注的对象而言,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些都是一种暴力。化用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一句话,我们或许可以说:“连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暴力。从事“援助交际”的少女,全天都在网络上直播的少女,徘徊在深夜街头、等待着所谓“神明”降临的少女,在“地下偶像”团体和女仆咖啡店打工的少女……横亘在这些少女的自我理解和研究者对于她们的“分析”之间的裂隙,几近于精神分析中患者和分析师的话语之间的裂隙。但上述类比仅仅到此为止:我并不认为这些分析和它们的分析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或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关系,我也不认为这里存在着精神分析必然伴随的移情;在我看来,倒不如说分析对象的存在本身(而非其矛盾混乱的、欲言又止的、扑朔迷离的自我解释),为分析者反思自身的历史性、反思自身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因此,尽管在内容层面两者无法沟通,但在形式层面,这类文学性的分析和它们的分析对象,其实共同揭示了一个总体性的当代文化—政治现状:如果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那么可以说,随着宫台真司所谓的人际交流的“岛宇宙化”愈演愈烈,能够为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所共享的交流基础越来越稀薄,曾经显得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种种关于“正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表象(以及其中包含着的权力关系),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让位于一个可称为“价值相对主义”(但未必等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图景——仿佛人生的各种选项,就它们都可以同样按照市场逻辑被归结于个人选择和个体责任而言,都显得同样可欲、同样正确、同样善好。如宫台真司所说:
在“不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眼中,“伦理主义式”行为举止,不过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大人们为了使他们相互间世代性的“信赖”不受到威胁,而在小圈子内进行的一种共同体仪式罢了。归根结底,在“不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看来,那些对他们说“要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之所以会说出这种话来,恰恰是因为他们属于自己并不接受的世界那一方。(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180页)
简言之,无论在伦理、社会关系还是技术的层面上,一个有机地关联起所有共同体成员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话)。不仅如此,关于这样一个世界的想象条件也逐渐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将“少女”视作一个统一而自洽的文化符号,并一厢情愿地将它和“革命”“纯洁”“无辜”“脆弱”等意指链条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还是将游走在所谓“正常生活”和“边缘生活”之间的少女化约为无法发声的、身世悲惨的待拯救群体的做法,距离鲁迅当年在小说《肥皂》中描写的那个道貌岸然、想法下流的老派知识分子四铭的举动,恐怕都只有一步之遥。(值得注意的是,《肥皂》中的四铭恰恰同时在上述两方面展开了对乞讨少女的想象。)而对于这一点,游走于白昼和黑夜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为生计奔波的少女们,无疑比书斋里的知识人认识得更切身,也更深刻。少女们难以捉摸的表情上,刻写着这个时代的秘密,刻写着我们自身的秘密。这个维度或刻度,我愿意把它称为“零度”。


